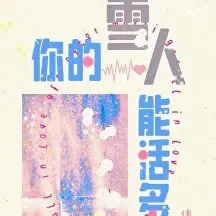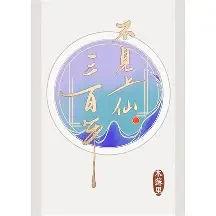激情年代: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
第一章:海外造势,赶搭回国末班车的无奈
1950 年的旧金山,华人街一间狭小的公寓里,江成正对着镜子整理西装领带。镜子里的人二十七八岁,梳着油亮的分头,脸上带着刻意营造的 “忧国忧民”,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《华侨日报》,头版标题赫然印着 “海外学子归心似箭,响应号召报效祖国”。
“江先生,船票准备好了,明天就能登上去香港的船,再从香港转道回内地。” 帮他办理手续的华人同乡推门进来,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,“您这‘海外高级工程人才’的名头没白造,听说内地特意给您评了七级工程师,回去就能当干部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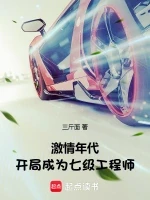
江成嘴角扯出一丝僵硬的笑,心里却在打鼓。谁也不知道,他所谓的 “海外留学经历” 水分十足 —— 当年家里凑钱送他来美国,本想让他学机械工程,可他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,混了五年只拿到个野鸡学院的结业证,连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眼看口袋里的钱快花光,又赶上内地号召留学生回国,他才动了心思,靠着在华人圈吹嘘 “参与过美国工厂设备改造”“熟悉精密仪器原理”,硬生生把自己包装成了 “稀缺工程人才”。
“可不是嘛,祖国需要我,我哪能在国外苟且?” 江成顺着同乡的话往下说,心里却满是忐忑,“只是…… 四九城那边人才太多,听说钱学森先生都回去了,我这点本事,可不敢在首都露怯。”
这话倒不是假话。江成早就打听清楚,回国的留学生里,不乏麻省理工、斯坦福的高材生,四九城的科研院所、工厂挤满了真才实学的大佬,他这 “半吊子” 去了,不出三天就得露馅。思来想去,他才定下主意 —— 以 “报效家乡” 为借口,申请回祖籍昌城。昌城是内陆小城,工业基础薄弱,大概率没人能识破他的底细,还能凭着 “七级工程师” 的头衔混个安稳差事。
同乡离开后,江成翻出藏在床底的纸箱,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,只有一本翻烂的《机械基础概论》和几张自己画的 “设备图纸”—— 这些都是他用来撑场面的道具。“赌一把了!” 他咬咬牙,把纸箱塞进行李箱,“只要回了昌城,先把架子搭起来,总能混下去。”
第二天,江成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。站在甲板上,看着逐渐远去的美国海岸线,他没有同乡们 “归乡报效” 的激动,只有对未来的迷茫与侥幸。他不知道,这场看似投机的归途,会在三天后彻底改写他的人生。
第二章:归途惊魂,火车上的魂穿转折
从香港转乘火车前往内地,再换乘去昌城的列车,前后折腾了半个月,江成终于踏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。这趟火车挤满了回乡的游子和支援内地建设的干部,车厢里人声鼎沸,行李架上堆满了箱子、包袱,空气中混杂着汗味、泡面味和淡淡的煤烟味。
江成的座位靠窗,刚坐下就觉得头晕 —— 他从小就晕车,更别说这绿皮火车一路颠簸,时速连四十公里都不到,铁轨接缝处的 “哐当” 声震得人五脏六腑都在晃。果不其然,火车开出没两个小时,他就忍不住趴在小桌板上干呕,脸色惨白如纸。
“同志,你没事吧?要不要喝点水?” 邻座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递过来一个搪瓷缸,男人穿着灰色干部服,胸前别着 “昌城机械厂” 的徽章,“看你样子像是读书人,是不是第一次坐长途火车?”
江成接过搪瓷缸,勉强挤出个笑容:“多谢同志,我…… 我确实不太适应颠簸。” 他不敢多说话,怕言多必失,只能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,可头晕越来越严重,到后来连眼睛都睁不开,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这一睡,就睡了两天两夜。期间他偶尔醒来,要么是被火车到站的广播吵醒,要么是被乘务员叫醒查票,每次都晕得天旋地转,连饭都吃不下,全靠邻座男人给的饼干充饥。直到第三天清晨,火车驶进一片山区,颠簸突然减轻,江成猛地睁开眼睛,只觉得脑海里 “嗡” 的一声,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。
“呃……” 他抱着头蜷缩在座位上,眼前闪过陌生的画面:宽敞的现代化工厂、精密的数控车床、电脑上复杂的工程图纸…… 还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,正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调试设备,嘴里念叨着 “这个零件精度不够,得重新编程加工”。
“同志!同志你怎么了?” 邻座男人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江成猛地抬头,眼神里充满了茫然。他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手(原主常年混日子,手比书生还嫩),看着车厢里复古的绿皮内饰,再想想脑海里那些 “现代化工程知识”,一个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念头涌上心头 —— 他,被魂穿了!
原来,这具身体的原主江成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,而他来自 2024 年,是某重工企业的资深工程师,因为一次设备调试事故,意外魂穿到了这个年代的江成身上。
“我…… 我没事。” 江成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快速梳理脑海里的记忆:原主的造假经历、昌城的工业现状、七级工程师的身份…… 还有自己掌握的现代机械设计、自动化控制、材料学知识。
“七级工程师…… 昌城……” 江成喃喃自语,原本的忐忑和侥幸消失得无影无踪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激动。原主想靠造假混日子,可现在的他,手握超越这个时代几十年的工程知识,或许真的能在这个激情年代,干出一番实事。
火车缓缓驶入昌城火车站,站台上挂着 “热烈欢迎海外学子回乡建设” 的红色横幅,几个穿着干部服的人举着牌子,其中一块牌子上赫然写着 “江成同志”。江成整理了一下衣服,挺直了脊梁,朝着站台走去 —— 这一次,他不再是那个 “混不下去” 的空壳,而是真正能为家乡建设出力气的七级工程师。
第三章:初抵昌城,七级工程师身份的压力与机遇
“江成同志!可把你盼来了!” 昌城工业局的王局长快步迎上来,紧紧握住江成的手,脸上满是热情,“我是工业局的王建国,专门来接你!昌城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!”
江成连忙回握,语气诚恳:“王局长客气了,我是昌城人,能为家乡做事,是我的荣幸。” 他刻意模仿着那个年代的说话语气,同时在脑海里快速回忆原主编造的 “专业方向”—— 原主说自己擅长 “机械设备改造与维护”,这个领域正好和他现代的专业对口,暂时不会露馅。
跟着王局长走出火车站,江成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解放初期昌城的模样:柏油马路只有主干道才有,两旁是低矮的砖瓦房,偶尔能看到几座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,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打补丁的衣服,自行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,偶尔驶过一辆卡车,都会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。
“昌城的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,主要就是一家机械厂、一家纺织厂和几家小煤矿。” 王局长边走边介绍,语气里带着急切,“就说机械厂吧,设备都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古董,精度差、效率低,上个月还因为设备故障停了三天工。你来了正好,先去机械厂当技术科长,负责设备改造,我们都盼着你能带来新东西呢!”
江成心里一紧。机械厂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糟糕,老设备改造看似简单,实则需要结合时代条件 —— 没有数控设备,没有新型材料,甚至连精密量具都稀缺,只能靠传统工艺和经验摸索。但他没有退缩,反而涌起一股斗志:“王局长放心,我一定尽力,争取早日解决设备问题。”
当天下午,江成就被送到了昌城机械厂。厂长李铁柱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,皮肤黝黑,手上布满老茧,见到江成时,眼神里带着期待,也藏着几分审视:“江科长,咱厂的情况王局长应该跟你说了,这几台德国产的车床,比我岁数都大,你看看,能不能想办法让它们‘活’过来?”
江成跟着李铁柱来到车间,轰鸣声瞬间灌满耳朵。几台锈迹斑斑的车床摆在车间中央,机床导轨磨损严重,齿轮箱里的油泥发黑,操作工正费力地转动手柄,加工出来的零件边缘粗糙,明显不符合精度要求。
“李厂长,先让操作工停一下,我仔细看看。” 江成戴上手套,蹲在车床旁,手指拂过磨损的导轨。脑海里的现代知识飞速运转:磨损严重的导轨可以采用 “刮研修复” 工艺,用刮刀手工修正精度;齿轮箱里的油泥需要彻底清理,更换适配的润滑油;至于零件精度问题,可以设计简易的 “靠模装置”,辅助操作工控制切削轨迹。
这些方法在现代看来是 “基础操作”,但在当时的昌城机械厂,却是没人想到过的新鲜办法。李铁柱和周围的工人看着江成熟练地检查设备,嘴里说出 “刮研修复”“靠模装置” 等专业术语,眼神里的审视渐渐变成了惊讶。
“江科长,你说的这些方法,真能管用?” 李铁柱忍不住问,“之前也请过几个技术员来看,都说这机床没救了,只能报废。”
江成站起身,语气肯定:“李厂长,您给我三天时间,我先画一套修复图纸,再找几个手艺好的老工人,咱们先从一台车床开始试修,成不成就看这三天。”
李铁柱当即拍板:“好!我把厂里最好的三个老钳工给你调过来,材料、工具你随便用,厂里全力支持你!”
看着车间里工人期待的眼神,江成深吸一口气。他知道,这是他在这个时代的第一份考验,也是他从 “投机者” 转变为 “实干者” 的起点。
第四章:扎根建设,用现代知识点亮家乡
接下来的三天,江成几乎泡在了车间里。他根据车床的实际情况,画出了详细的 “刮研修复” 图纸,标注出每一处需要修正的精度要求;又设计了简易 “靠模装置” 的草图,用薄钢板和螺栓就能制作;同时,他还手把手教老钳工如何使用刮刀,如何判断刮研后的精度是否达标。
老钳工们起初还有些不服气 —— 一个 “留洋回来” 的年轻科长,能比他们这些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懂行?可跟着江成干了一天,他们就彻底服了。江成不仅能说清 “为什么要这么刮研”“精度误差控制在多少合适”,还能亲自上手示范,刮刀在他手里灵活自如,刮出来的导轨表面光滑,精度用百分表一测,竟然真的达到了加工要求。
“江科长,您这手艺,比德国专家都厉害!” 老钳工张师傅忍不住赞叹,“我干了三十年钳工,还是第一次知道,磨损的导轨还能修得这么好!”
江成笑了笑:“张师傅,这不是我厉害,是工艺方法的问题。咱们以前修设备靠经验,现在结合科学的测量和修复工艺,效果自然不一样。” 他知道,要想真正带动厂里的技术进步,不能只靠自己一个人,得把这些方法教给更多工人。
三天后,第一台修复后的车床正式试运行。当操作工按照江成设计的靠模装置,加工出第一个精度达标的零件时,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李铁柱拿着零件,激动得手都在抖:“成了!真的成了!江科长,你可是救了咱们厂啊!”
消息很快传到了工业局,王局长特意赶来视察,看到运转正常的车床和精度合格的零件,对江成赞不绝口:“江成同志,你真是给昌城立了大功!下一步,你有什么打算?”
江成早就有了计划:“王局长,我想在厂里办一个‘技术培训班’,把设备修复、精度控制的方法教给更多工人;另外,我还想设计一套简易的‘半自动送料装置’,装在车床上,能提高加工效率,还能减少操作工的劳动强度。”
这个计划得到了工业局和机械厂的全力支持。技术培训班很快办了起来,江成把现代机械基础理论和传统工艺结合起来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,还亲手示范操作,工人们学习热情高涨,车间里的技术水平肉眼可见地提升。
半个月后,第一套 “半自动送料装置” 安装在了修复后的车床上。原本需要操作工手动推送的工件,现在靠装置自动送料,加工效率提高了一倍,操作工也不用再长时间弯腰用力,车间里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江成没有停下脚步。他发现厂里的原材料浪费严重,就设计了 “零件套裁方案”,根据零件尺寸优化原材料切割方式,每月节省钢材近一吨;他看到纺织厂的纺纱机经常断纱,就主动上门,设计了 “纱线张力调节装置”,解决了断纱难题;甚至连郊区的煤矿,他都跑去出主意,设计了简易的 “矿车轨道防滑装置”,减少了矿车事故的发生。
短短半年时间,江成的名字在昌城传遍了。人们不再记得他是 “海外回来的七级工程师”,而是亲切地称他为 “江师傅”,不管是工厂的设备问题,还是农村的农具改造,大家都愿意来找他出主意。
1951 年春节,江成收到了工业局颁发的 “昌城建设模范” 奖状。站在领奖台上,看着台下熟悉的面孔 —— 李铁柱、张师傅、王局长,还有车间里的工人、纺织厂的女工、煤矿的矿工,他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
“我刚回来的时候,其实……” 江成握着奖状,突然想坦诚自己的过去,可话到嘴边又改了口,“我刚回来的时候,担心自己做不好,辜负大家的期待。但现在我明白了,只要真心为家乡做事,把学到的知识用在实处,就一定能做出成绩。”
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,掌声里满是认可与敬意。江成看着窗外飘扬的五星红旗,心里无比坚定。他知道,这个激情燃烧的年代,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;而他,也将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,在这片家乡的土地上,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建设故事,为这个时代添上一抹明亮的色彩。
春节过后,江成接到了新的任务 —— 参与昌城第一家小型化肥厂的筹建。他拿着设计图纸,站在空旷的厂址上,看着远处赶来支援建设的工人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新的挑战已经开始,而他,早已做好了准备。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激情的年代,他这颗 “意外坠落的种子”,终于在祖国的土壤里,扎根、发芽,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枝叶。
以上是关于激情年代: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的内容和剧情介绍,更多详情请下载激情年代: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TXT版本阅读。


![一级律师[星际]小说全本下载-一级律师[星际]txt免费下载](https://www.zlibraryrukou.com/uploads/202601/18/d744e1fcb899a8c7.webp)